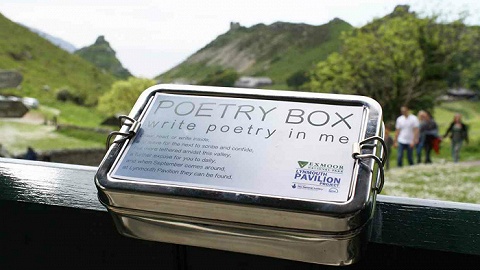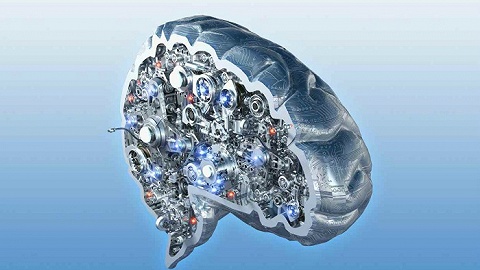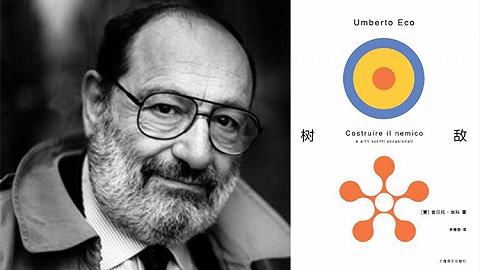8月29日,《新京报》刊发两版独家报道《读经少年圣贤梦碎:反体制教育的残酷试验与读经教主王财贵的产业链条》,起底“读经热”这种反体制教育的失败,勾勒出一条以王财贵为主导的读经教育产业链条,迅速引起舆论热议。
“读经”到底是不是一种国学教育?会对孩子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目前,我国的“读经”教育处在什么样的发展局面?造成了什么样的社会影响?反体制的读经运动真的能为我们的教育带来希望呢?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同济复兴古典书院院长柯小刚数年来守望在“当代儒学教育”第一线,他认为:目前的情况恰恰是极端的体制化、僵化和“应试化”。读经运动只不过是把体制内基础教育的内容完全替换为传统文化经典,而且是不允许讲解的、强迫背诵的、意义锁闭的、僵化的经典。读经运动本身很可能是一种现代性病症的体现。我们所追求的“儒学教育”应该是日新其德的“儒学”与充满可塑性的“当代社会”之间的张力、对话、批评性建设和建设性的批评。
本文为柯小刚在首届上海儒学大会上的演讲,有删节。

近年儒学发展非常快,成绩很多,问题也不少。这个时候开会非常及时,可以总结经验,讨论问题,展望未来。我觉得儒学界应该引入更多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要和而不同,不要乡愿,形成良性互动,这样才能长期健康发展。
去年暑假我参加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的工作坊,曾谈到儒学自古就有非常强的批判传统,是一种富有建设精神的批判理论和实践智慧,今天想就一些现实问题具体展开一下。
今日儒学复兴被太多敌意和误解包围,困难重重。儒学界的任何微小偏差和失误都有可能被蓄意夸大,变成儒学复兴的障碍。不过,这同时也未尝不是一种督促。
在虎视眈眈的注视下,复兴儒学的最好方式不是互相吹嘘、隐瞒缺点,当然也不是互相拆台、恶意批评,而是要发扬“和而不同”、“过失相规”的良性自我批评传统,加强自律,有问题自己先提出来改正,才能更好地面对外界批评。
万一有儒学界自我批评不到的地方,外界指出,我们也应虚心接纳,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有辩则言,无说则默,莫不从善如流也。

一
当代社会的儒学教育
我今天想谈的主题是“当代社会的儒学教育”。这个题目可以有两种读法:一种是“儒学教育在当代社会”,一种是“儒学教育当代社会”。前一种是名词的读法,后一种是动词的读法。
名词的读法是静态的思路,把“儒学”理解为一套现成的传统文化教条,把“当代社会”理解为一套固定的结构形态。所以,这种思路必然会把“教育”理解为“宣传”和“灌输”,即“把一套现成的价值观灌输到一个固定的社会形态里面去”。
相反,动词的读法则是“生成论”的思路。它首先把“教育”理解为一个动词,理解为生命的成长过程、社会的形成过程。所以,对于这种思路来说,“儒学”并不是一套现成的僵化体系,而是一种动态的朝向历史经验和未来可能性开放的生命学问,“当代社会”也不是一种僵固的结构形态,而是充满可能性和可塑性的“生成之物”。
从上述两种读法出发,“当代社会的儒学教育”可以有三种可能的立足点。
一个立足点是固化的“当代社会”,一个立足点是现成的“儒家”。立足于这两个点之上的教育思想都是名词化的、静态的思路,本质上可能都不是真正的教育,而不过是宣传和灌输,无论其立场是迎合当代社会还是批判当代社会,无论其宣传和灌输的形式有何不同(这一点后面还要详细分析)。
第三个可能的立足点便是作为生命学问的动词化的“教育”。在这个意义上,教育不只是一个“专业领域”,而是“人之为人”、“社会之为社会”的根本存在论、政治学。
从这个意义上的“教育”出发,“儒学教育”才能回归其作为一种“人的养成”意义上的生命教育,从而与当代社会的“工具培训”(包含现代国家公民培训和现代企业劳动力培训等)形成一种有益的张力,通过一种批判性的教育实践来参与当代社会的建设,帮助现代社会提高“工具培训”的质量。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或许可以说,所谓“当代社会的儒学教育”,就是日新其德的“儒学”与充满可塑性的“当代社会”之间的张力、对话、批评性建设和建设性的批评。
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儒学和儒家学者的自我教育过程,以及当代社会的气质变化过程。于是,教育不再被理解为一种工具性的培训手段(即使培训内容是“儒家价值观”),而是教育者和被教育者“教学相长”的共同成长。
从名词读法的静态思路出发,“当代社会的儒学教育”或可区分为四种形态:基础教育体制中的传统文化教育、反体制的儿童读经运动、体制内的大学传统文化教育和研究、面向成人社会学员的国学培训。
这四种形态是体制内外、成人儿童的两两组合。这四种形态虽然年龄不同、体制内外有别,但却共享高度一致的缺点:僵化。
体制内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中的儒学因素正在逐步加强。然而,体制的僵化已经深入骨髓,以至于在体制教育的设计者那里,所谓“当代社会的儒学教育”并不意味着对于“什么是教育”的根本反思和重新学习,而只不过是换一下教学内容,或者增加一点儒学经典课文的比重。
至于教学方法,仍然沿用一种与真正的儒学教育、古典博雅教育格格不入的“宣传”、“灌输”、“应试教育”。“儒学教育”是否首先意味着“教法”、“学法”乃至“活法”的自我教育、自我提升,完全没有进入僵化体制的视野。
那么,反体制的读经运动是否带来希望呢?很遗憾,目前的情况恰恰是极端的体制化、僵化和“应试化”。读经运动只不过是把体制内基础教育的内容完全替换为传统文化经典,而且是不允许讲解的、强迫背诵的、意义锁闭的、僵化的经典。

反体制的读经不但没有解决体制教育的灌输教育问题,反而发展出一套更加极端、更加野蛮的灌输方法:全日制封闭背诵,每天八小时,连续十年,单纯背诵,不允许讲解,不学其他课程。
应试教育问题同样如此。千千万万读经的孩子确实不用参加体制内的考试了,也因脱离学籍而无法参加体制考试了,但他们现在有了另外一种“考试”方法:一本接一本地录制“包本背诵”视频(一本书从头到尾连续背下来叫“包本”),以便升入一所书院听“解经”。背书十年(3-13岁),包本背诵百万余字(严格来说不是百万余字,而是一百万个意义锁闭的音节组合),千万人过独木桥,然后才有听讲经义的机会:这是比体制内“应试教育”还要残酷的“应试教育”。
那么,体制外面向成人社会学员的国学教育呢?是否情况乐观一点?这里确实不存在强制问题,因为社会成人学员都是自己真的想补传统文化的课,积极性很高。然而,这些年来的“国学热”提供了什么儒学教育呢?很遗憾,都是一些毫无批判性的迎合当代需求的国学文化消费。在这一点上,读经运动反而显得更有当代的批判性,虽然他们滥用批判,把儒学固有的“建设性的批判精神”极端化为宗教形式的“反体制运动”。
无论是成人国学热的完全迎合当代社会的鸡汤化,还是读经运动的完全对抗当代社会的激进化,都未能保持“儒学”与“当代社会”之间的健康张力、良性互动。
国学热是立足自我固化的“当代社会”(实际当代社会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固化,而是充满了变化气质的可能性),用一种鸡汤化的“儒学”来为当代人的文化消费口味服务,丧失了儒学的批判性,同时也就丧失了儒学真正的建设性作用;读经运动是立足于自我僵化的“儒学”(儒学本身并不是僵化野蛮的东西,而是活泼泼的生命学问),用一种高度体制化的“读经教育”来批判当代教育体制和社会价值观,丧失了儒学的建设性,同时也就丧失了儒学真正的批判性作用。
无论丧失批判性还是建设性,都会丧失“儒家”和“当代社会”之间的良性张力,丧失真正的“儒学教育”品格。一种“儒学教育”形态,无论它是立足于自我固化的“当代社会”之上,还是立足于自我建构出来的一种僵化“儒学”之上,无论它是为了“服务当代社会”还是“弘扬儒学”,都将错失真正的“儒学教育”。

真正的儒学本身就是生命成长的学问,或者说就是教育的学问。这种意义上的教育是《易经》蒙卦所谓“山下出泉”的“发蒙”,是陶冶涵泳、变化气质,是新旧之间的健康张力,是生命本身的自我突破和成长。
“发蒙的教育”是从人的生命成长经验中体贴出来的教法,深具道学的性质:它不期望通过大面积的运动形式宣传某种主张、培训工作技能(“小人的然而日亡”),而是结合各种可能的具体形式,因势利导、潜移默化地渗透进去,“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导而弗牵,开而弗达”,发人端绪,使其自成,勿忘勿助长,闇然而日章。
二
关于读经运动的八点疑问
从“发蒙”的教育思路来看,近年来日益风行的“国学热”和“读经运动”,运行在文化革命-商业传销-政治宣传“三位一体”的“社会运动”轨道上,创造了越来越简单化、可复制的连锁读经培训模式,以及越来越成熟的“国学文化产业市场”。
这些东西貌似属于“传统文化”,实则毫无古典心性,完全是从属于现代生活方式的一点“古典文化消费”、“国学心灵鸡汤”。它们的制造和传播机制完全走在“启蒙式的”、“景观社会的”、“大众文化的”轨道之上。
当然,无论其中存在多少问题,“国学热”和“读经运动”非常成功地在这个“拼数量”的当代社会吸引了数量巨大的人群来积极支持传统文化、热情学习儒家经典。一百年来备受摧残打压的传统文化第一次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大众支持,这是划时代的成就,功不可没。
同时毋庸讳言,“国学热”和“读经运动”作为传统文化复兴的初期发展带有非常浓厚的民间通俗文化色彩乃至民间宗教色彩。其中做得比较好的项目,譬如某电视台的著名国学节目,问题还只是出在低智化、娱乐化、鸡汤化,即使有些知识性错误倒也无伤大雅;但有些较差的项目,譬如近年来日益流行的愚昧读经、野蛮背诵(全日制专门读经,十年不许讲解,只能背诵,每天背书八小时以上,不允许读经典白文之外的书籍,包括古人注疏也不许看),则必须认真检讨一下了。
与很多儒家学者一样,我对这些“热”经历了一个态度转变的过程。起初自然是抱一种同情的态度。经历百余年来的反复摧残,传统文化教育几度中断,所剩无几。体制内教育中仅存的一点古文也往往是在非常任意武断的所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方针指导下的阉割残废经典,以及基于各种现代性偏见的片面讲解。学生有权利了解真实全面的华夏文明。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主张全日制忠实背诵经典原文的做法构成了一种重要的补充,弥补了体制教育的缺陷,也为那些希望读到未经阉割、未经现代人歪曲解释的完整经典的学生和家长提供了一种选择,功不可没。

然而,过犹不及。当我在儒学教育第一线接触到越来越多读经老师、读经家长和学生,了解到一些实际情况之后,发现问题不少。主要问题有如下八点:
一、全日制读经,彻底脱离现有基础教育体制,只读经和其他传统文化,不学数学、英语等其他课程,好不好?(有些学堂有英文经典背诵,但是在字母都不教的前提下进行的,学生对所背英文经典一句都不懂。还有梵文经典背诵也是这样。)
二、如何读经?只背诵经典白文,不读传、注、疏,好不好?
三、背诵是好方法,古代有效,今天仍然有效。不过,是否需要背那么多(四书、诗经、尚书、三礼、春秋三传、易经、黄帝内经、道德经、庄子、莎士比亚英文全集等等)?有否必要“包本”(从头到尾一口气背完一本书)?有否必要为了突出背诵的重要性而片面排斥理解?
四、究竟什么是“背诵”?在完全不予讲解的情况下“包本背完一本书”是不是真正的“背诵”?甚至在不认识一个英文字母、不懂一句英文的情况下“背诵莎士比亚剧本的原文”是不是真正的“背诵”?记住毫无意义的音节顺序是不是“背诵”?
五、背诵和理解能否截然划分?经典白文和注疏能否分离?单纯背诵十年(大概3-13岁),不许讲解,13岁之后才开始“解经”,如此机械地划分读经阶段是否合理?如果十年没有启发式教学、理解力和想象力的训练,只是机械背诵,即使到十三岁的时候能倒背如流,学生是否还有理解经典、思考经典、发挥经义的能力?尤其是,如果这些孩子十年之中都是在一种封闭的环境中日复一日地重复背诵那些毫无意义的音节,严重脱离社会现实,当他有机会开始理解经典和解释经典的时候,即使他尚有理解和解释能力,他能在他的经典解释中融入时代问题的思考,做“活的经学”吗?至于那些无意做学问的读经毕业生,问题更麻烦:他能有效地融入当代社会吗?
六、儒家经典本来是生命的学问,是从先王历史和圣贤生命中生长出来的活泼泼的生命学问。儒家经典的学习方法是不是应该采用《论语》中比比皆是的对话式、启发式、情境化的教学?也就是前面谈到的“发蒙”的教学?“读经规划”的“背诵十年、解经十年”貌似是对现代体制教育的抵抗,实则是比现代教育体制更加僵硬、更加机械化的极端现代化和粗暴体制化。
七、读经运动的理论基础“教育简单论”是否可信?“做读经老师不需要有文化,不用讲解,也不许讲解,只要会按复读机按钮、督促小朋友背诵,就是最好的读经老师”,“小朋友读经是最简单不过的事情,不需要讲解,不需要读注疏,只需熟读经典白文一百遍,一千遍,直到能背诵即可。先只管背,背十年,十年后全部会背了再讲解”……这些在“读经圈”流传甚广的说法是否可信?
八、读经运动圈中广泛流行的“读经万能论”是否可信?“数学不用学,只要背熟经典,半年就能学会全部中小学数学”,“英语不用学,字母、发音、语法都不用教,只需背熟莎士比亚,将来到国外就会说英语,而且是高级英语”,“不用学那么多课程,背熟经典就能上清华北大哈佛耶鲁”,“什么都不用学,从小只需要背熟经典,不用讲解,长大后在生活中遇到事情会突然想起经典的句子,自然会养成君子人格,乃至成为圣贤”……这些在“读经圈”耳熟能详的基本教义是否可信?

三
背诵、简单可复制与反现代性的吊诡
提出上述八点问题不是拆台、找茬,更不是“判教”,搞“大批判”。提出这些问题与其说是在问难谁,还不如说是儒学教育界的自我反省、自我批评。儒家向来勇于自我检省,三省吾身,日新其德,还没有弱到讳疾忌医的地步。这些问题也不只是我个人提出的问题,而是很多儒学界朋友共同发现的问题,提出来只是为了引起讨论,促进发展。
清末废科举、民国废读经科以来,经典教育命途多舛。今日重提读经,应该怎样做才有利于良性发展?儒学界应鼓励多种探索,也要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发现问题,自我批评,改正偏差。
儒学界的自我批评不是打倒读经,而是帮助读经。如果儒学界内部不发展良性的自我批评,不敢自我反省,发现问题也不讲,等到问题闹大了,官方出来取缔了,媒体开始讨伐了,整个儒学界都会受连累,圣贤经典也将再次遭受误解和污蔑,我辈岂不是儒学罪人、乡愿小人?哪里配得上“儒士”之名?
读经的意义自不待言,功德无量。但如何读经却值得思考、实践,总结经验教训,调整方式方法。
目前读经运动的关键问题集中在“背诵”。时间有限,我只集中谈下“背诵”的问题。背诵毫无疑问是非常有效的经典学习方法,我从小就自发地热爱经典背诵。我出生在文革后期的农村,几乎在文化荒漠中长大。我如饥似渴地背诵能找到的任何美好的句子。我从小的语文成绩和作文成绩得益于我爱好背诵的天性。

然而,在接触了一些读经运动实际情况之后,我开始思考一个从来没有思考过的奇怪问题:究竟什么是背诵?这本来不是问题,然而读经运动的独创教法逼使我不得不思考如此奇怪的问题。
我听过一些读经学生“背诵经典”。我发现这些孩子不但不懂所背的文句是什么意思,而且甚至不能清晰地读出他们自己所“背诵”的句子。他们只会用一种非常快速而模糊的发音去重复那些似是而非的音节。你甚至很难区分他们“背诵”的是中文经典还是英文莎士比亚或梵文佛经(后者也是被要求背诵的,而且竟然是在不认识字母的情况下要孩子“背诵”)。
你如果要求他们缓慢而清晰地背诵,他们就一句也背不出来了。更有意思的是,如果你提第一句,他可以快速而模糊地“顺到”到最后一句,但如果你从他“会背”的经典中任意抽取一句,问他下半句是什么,他就答不上来了。
所以,这根本就不是背诵,而是一种类似于摇头丸效果的摇滚rap。我从小就背课文、背英语,大学以来也背诵过儒道经典。背诵是非常好的学习方法,但那些孩子用一种极为快速而模糊的发音“嘟嘟嘟嘟”地摇滚出来的东西,不过是一些被迫记住的毫无意义的音节组合。
这种所谓的“经典背诵”被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重复,十年之中不允许读任何其他书籍,不学其他课程,直到这个孩子可以在摄像机前连续“嘟嘟嘟嘟”地“背诵几十万字的经典”(拍摄背书视频是他们的考试方法),实际上是要他重复几十万个毫无意义的音节组合。
他因为不懂这些音节组合是什么意思,自然无法清晰地说出其中的任何一句话,更不可能在将来需要的时候引用经典文句。
我见过一些曾经在读经学堂“背过几十万字经典”的孩子。一个月不复习那些音节组合,他们就忘记了。当然,我接触到的读经学生有限,可能会有更优秀的学生,真正能清晰明白地背诵经典的学生。
不过,可想而知,太过功利性的、强度极高的“背诵目标管理”会把一个孩子弄成什么样子。一月背多少万字,一年背多少万字,三年背多少万字……每背下来一本就及时录像保存,作为“包本背诵”的证明,然后冲刺下一本,等到下一本背完,前一本早就忘得精光。
而且,在这些年中,一本一本的包本背诵录像成为唯一的学习目标。如今,遍布城乡的数千家读经学堂都在夜以继日地倒计时,驱使学生狂热背诵,明确的目标是录制包本背诵视频,以便有资格升入一个书院听“解经”。
这些学生被要求每天诵经八小时以上(我见过因此落下哮喘病的学生),普遍处在一种非常癫狂的状态。我去过这样的读经班现场,其紧张程度和无意义指数远超高考题海战术。高考复习做题虽然紧张,还略有智性愉悦,毕竟做题是要思考和理解的,而不许理解的机械音节背诵则是彻底无意义的事情。
对于这些读经学生来说,经典的丰富意蕴都是锁闭的。别说十年,恐怕三五年下来,多么聪明的学生也会变傻,多么热爱经典的学生都会心生厌恶。到那时,恐怕你给他讲解经典,他也没有能力听懂,或者没有兴趣听了。
当然,天性好学的学生会因此激发出更加强烈的求知欲,想一探究竟,那些背了几年的经典文句到底是什么意思?不过,经过多年的智力发育停滞和与世隔绝的封闭读经,他们能理解到什么程度仍然是不容乐观的。

第一批经过多年背诵的孩子已经在接受解经教育,他们几年后即将毕业。按照读经运动的宣传,他们中将诞生一批圣贤君子和经学大师。读经教育的结果即将揭晓,成千上万学生家长和社会公众都在等待最后的惊喜。我自然也希望从中诞生大师,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但我更担心的是,如果结果令人失望,那些曾经的狂热支持者有可能会被激怒,转而过度批评读经运动,甚至否认读经的意义,加上蓄意攻击传统文化的大众媒体推波助澜,有可能出现崩盘效应,给整个传统文化复兴事业带来负面影响。我已经见到一些读经家长开始对读经运动的结果表示焦虑。
宗教化的发展模式总是难免信徒信心的变化问题。儒学教育下学而上达,发蒙而疏通知远,本来就不应该建立在这种宗教化的宣传和“启蒙-启示”之上。这种宗教化形式的蓬勃发展必然只是传统文化复兴初期的现象,未来一定会复归平正,气象正大。
这种貌似背诵而实非背诵的经典教学方法无疑是荒谬的,并不是儒家传统的读经方法。我见过一本经典背诵教材的序言中,编者明言:最好的读经老师不是人,而是复读机,或者会按下复读机power on/power off的人。如此明显荒谬的“读经方法”为什么风行全国(保守估计有几千家读经学堂,遍布城乡)?只能归咎于传统文化土壤的贫瘠、教育生态的畸形。
读经运动的产生,诚然是出于对现代社会问题的反思,尤其是对现代体制教育的反动,但吊诡的是,读经运动本身很可能是一种现代性病症的体现。
读经运动的推动者反复宣传读经是简单的,无需理解,只需背诵,起初很可能是出于师资缺乏的无奈之举。但当他们发展简单可复制的连锁模式的时候,简单化、数量化、标准化就成为一种现代快餐企业的必备商业技术了。这个案例告诉我们,“当代社会的儒学教育”是多么困难的一个话题。所有现代性的批判都有可能走向其初衷的反面。
十多年来,我自己也一直在探索在当代社会实践经典教育的现实可能性。道里书院、同济复兴古典书院也是问题重重,教训多于经验。其中最基本的一点体会是:现代性批判不宜采用现代惯用的运动形式、革命形式、非此即彼的激进形式,而应该回到因势利导、潜移默化的古典品格,用保守的态度做保守的事业,不要用激进的态度做保守的事业。
“君子闇然而日章,小人的然而日亡。”千百年后,千百年前有的仍然有,千百年前没有的仍然没有。现代性的激进和喧嚣不妨当戏看。读经运动作为反现代性的现代性,亦作如是观。

四
“发蒙”、“包蒙”:从内部转化当代社会的儒学教育
所以,我想回到起初的话题:《易经》所谓“发蒙”、“包蒙”的教育如何可能?“发蒙”意味着因势利导的道路探索,“包蒙”意味着建设性的批判精神。不放弃儒学的批判性,保持对现代性的批判立场,但不激进地对抗和抛弃,而是进入它,从内部转化它,可能是“当代社会的儒学教育”未来的任务。
现代国家的公民培训、现代企业的劳动力培训是现代教育不可消解的基本目标。儒学教育的批判性并不体现在反对现代公民培训和劳动力培训,而体现在不满足于把教育降低为纯粹工具性的培训,从而丧失“人之为人”的基本属性,以及由此导致公民培训的败坏、劳动力培训的异化。
当代社会的儒学教育作为一种批判性的社会建设实践,其批判性体现在对工具化培训的抵抗,其建设性体现在:通过对工具化培训的批判,而且是通过一种渗透到现代培训体系内部的潜移默化式的实践批判,帮助当代社会把“工具培训”提升为“人的教育”,从而取得更好的培训成果。
只有通过当代社会的儒学教育培养出“人”,现代国家才能培训出真正自由的、自我负责的、有德性的公民(现代所谓“自由”根本配不上真正属于人的自由),而不只是低质量的“守法公民”;只有通过当代社会的儒学教育培养出“人”,现代企业才能找到真正自由的、幸福的生产者,而不只是“能创造财富的人力资源”。
以一种批判的姿态介入当代社会,儒学教育反而能更好地帮助当代社会。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儒学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的形象。在每个时代,儒家都是不合时宜的诤友。帮助你,但不讨好你。批评你,但是爱你。
因此,对于弊病丛生的现代教育体制,儒学教育可以而且应该保持批判性,但不宜像读经运动那样对此采取一种激进的“保守主义革命”态度,谋求完全脱离现代国家公民培训体系和现代企业所需的劳动力培训体系,另起炉灶,用一种与世隔绝的形式做全封闭全日制的纯粹经典背诵班。
这种模式的危险在于,它的初衷是为了对抗现代性,但结果恰恰可能变成一种现代性,而且是畸形的现代性。

我相信读经运动的倡导者是诚恳热情的儒家同情者和志向崇高的教育家,但我希望他们多一些冷静的理性,多一些自律,加强读经学堂和老师的监管,不要再宣扬“教育简单论”、“读经学堂谁都可以开,读经老师谁都可以做”的不负责言论,不要为了追求数量扩张而降低品质,辱没斯文。
我相信儒学经典本身有抵抗畸形现代化的能力,但当代儒家有责任看到危险的可能性。尤其是当这样一种决绝地反对现代教育体制的读经运动拥有了成千上万追随者、已经成为一种大规模社会运动的时候,我宁愿冒着说错话的危险在此提出我的担心。
我衷心希望我的担心是多余的,我今天的发言完全是错误的。如果我的担心不属多余,发言尚有可取之处,我希望儒学界能负起学者应有的责任,帮助读经运动拨乱反正,走上正轨。如果有更多学者能行动起来,向读经运动的倡导者学习,效仿他们投身基础教育的热情和勇气,探索多种可能性,为当代社会的儒学教育奉献自己的学识,就更好了。
十多年来,我也做过很多形式的探索:读书会(包含线上线下)、会讲、讲座、论坛、工作坊、大型系列课程和小型特色课程(以十三经为主,涵盖经、史、子、集选读,以及书画、中医等修身内容)、国学师资培训班、少儿古典班、经典研究丛书出版等等。我们的学员来自各行各业,有成人也有小孩,所有活动都是公益的。
我总是首先把自己理解为一个普通读书人和教师,其次才是学院的学者和教授。“普通”是社会的和人类的,“学院”是特定职业的。我从不参与学院学术资源的争夺,但也不刻意排斥“体制”。我一直尝试在体制内做体制外的事情,在体制外做体制内的事情。子曰“有教无类”,教育本来应该是打成一片的事业。
理性地公开运用、观察与批评是学者的天职;站到社会教育的第一线,践行大众教化,更是儒家士大夫的当代责任。学院学者办社会教育难免有其局限性,所以,我在此恳请学界同仁和社会公众对我的实践探索予以批评指正。
我上面所讲对于读经运动问题的观察和思考,不是说他们做得不好、我做得好,而是希望引起体制内外的良性互动,以及儒学界内部的良性自我批评。我对读经运动的观察和问题分析难免有错,我自己的社会教育实践也难免问题重重。我今天来谈读经运动的问题,目的不在针砭他人,而在提醒自己。
我们每个人都深处当代社会的困境之中,没有任何人能简单摆脱“启蒙未遂的坏病”所导致的现代性吊诡。在恢诡谲怪的吊诡处境中,团结很重要,而自我检省和互相批评可能更是“悬解”的佩觿。诗云“容兮遂兮,垂带悸兮。”童子永远是无辜的、开放的、可塑的。儒学教育如能解开现代性的死结,未来就仍然是充满希望的。
本文转载自公号探索与争鸣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