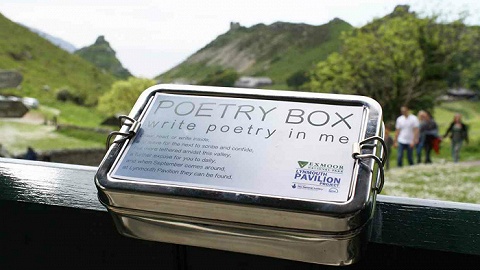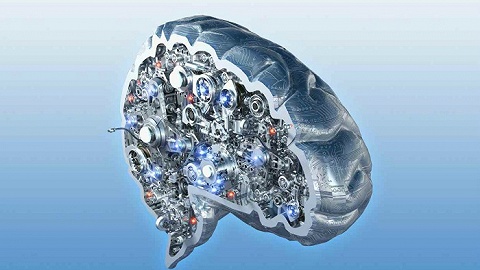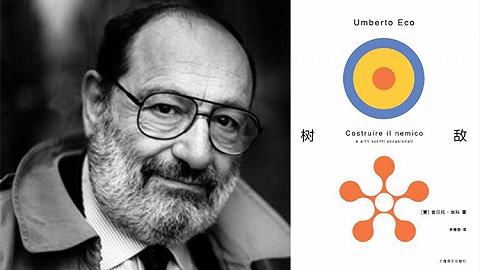根据斯特金定律(Sturgeon’s Law),任何事物的90%都是垃圾。这句名言出自1950年代的著名科幻小说家西奥多·斯特金(Theodore Sturgeon),他曾说道:“人们常常抨击道,90%的科幻小说都是垃圾,然而这种论调毫无意义,因为其实科幻小说的质量与其他所有艺术作品一样。”解读斯特金这一席话的重点在于,你如何定义什么是“垃圾”。
在爱丁堡国际图书节上,为期10天的讨论环节都被同一个话题所占据:如何定义青少年文学(young adult fiction)。在激烈的言辞交锋中,有人提出了这一定律。尽管讨论历时数日、如火如荼,尽管有弗朗西丝·哈丁(Frances Hardinge)、马库斯·塞奇威克(Marcus Sedgwick)、西蒙·梅奥(Simon Mayo)等文学名家各抒己见,然而人们还是没能讨论出最终的结果,就连写青少年文学的作者自己也无法给此类型文学下一个妥适的定义。
这类文学作品的兴起是从1950年代苏珊·艾罗依·辛顿的《局外人》(SE Hinton’s The Outsiders)开始的吗?亦或是受1960年代艾伦·加纳(Alan Garner)等作家的影响?或许关于它的定义从未有一个固定的结论,而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改变,每一代作家都以独特的风格重新定义这类文学。不过有趣的是,这些作家往往不是专门为了青少年而进行创作,而是纯粹根据自己的想法下笔。
在8月29日图书节的“青少年文学大讨论”中,话题五花八门,如何定义青少年文学的种种相关议题层出不穷,每当一个话题引起热议时,人们的注意力又会被另一个话题吸引。那么,青少年文学究竟算一种文学大类,还是只能算一种小类?它的读者群体是谁?它的内容是否过于成熟?是否质量堪忧?是否不够有趣?
为了缓解讨论的紧张气氛,青少年文学作家安东尼‧麦高恩(Anthony McGowan)抛出了斯特金定律:90%的青少年文学都是垃圾。他表示,就青少年文学的受众群体来看,这更像是一个教派,而非文学类别。他在会议中表示,青少年文学的读者大部分都是年长白人女性,价值观与审美观十分单一。因此,有些人开始质疑,大部分青少年文学网络写手都是女性,编辑也以女性居多,导致“这类作品很符合二三十岁女性的口味,而不是青少年。在这个以女性为主导的领域里,创作出的作品都是反应她们自身的经历,是写给年轻女性看的”。然而,做出此结论的人似乎并未意识到性别与心思细腻程度的关联性,这才是此类作品的关键之处。
青少年文学或许称不上是一种文学大类,但正像许多关于文学类别的讨论都会涉及到价值评判一样,关于青少年文学的辩论也渐渐演变成了价值评判。麦高恩坦言:“我觉得成年人不应该阅读青少年文学这种无病呻吟的小儿科作品。而应该多读点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狄更斯等名家名著,别再整天捧着《暮光之城》和《饥饿游戏》魂不守舍。这才是成长的标志,应该读点有深度的书。”不过,伊丽莎白·韦恩(Elizabeth Wein)和菲利普·沃马克(Philip Womack)对此观点不以为然。
作家帕特利斯·劳伦斯(Patrice Lawrence)反击道:“我49岁了,已经走过了人生的大半,剩下的日子并不算多了,但我绝对不会把剩下的这部分生命浪费在读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上!”这番言论引来了听众的一片掌声。
一位年长的女读者正排着队等待哈丁在她的《谎言树》上签名,她激动地说:“我非常非常愤怒,他擅自主导了这届图书节的舆论,根本没人来问问我们这些读者是如何定义青少年文学的。”她身旁的另一位中年女性读者表示同意。
青少年文学作者们谈及自己的青少年读者们,总是不吝赞美之词,然而,他们却每每否认自己的书是专门为青少年群体而创作的。这正是麦高恩所称的矛盾之处。如今的青少年文学读者已经不仅仅局限于青少年了,当你来到图书节上的摊位时,会发现成人展区与儿童展区竟然摆放着同一本书。杰妮·唐纳姆(Jenny Downham)在“青少年文学大讨论”中分享了自己的经历,她曾在青少年小说书柜与成人小说书柜上同时看到了自己的作品《我死之前》,她回忆道:“我觉得这种行为蠢极了。”不过话说回来,从营销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增加销量的明智之举。
那么,这场关于青少年文学的会议到底讨论出了什么结果呢?韦恩对此写道:“我觉得所有话题都是老生重谈,并没有什么新意,只是大家都很享受这个吐槽的过程罢了。”难道我们就不能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好好讨论青少年文学吗?难道青少年文学市场就真的被良莠不齐的女性作者占领了吗?
除了斯特金定律以外,还有一个定律很符合目前的状况:奥卡姆剃刀定律,亦即,最简单的解释方法往往才是最正确的。运用在青少年文学上,简单来说,此类文学其实体现的是一种自我反省的过程。正如我们平常收看的电视节目、喜爱的艺术类型、阅读的书籍,这些精神食粮都在提升我们的素养和品味。
当读者群里包括孩子时,这就更重要了。所有父母都希望书籍是具有教育意义的,并不仅仅是读着好玩的。其实作者也一样,他们也都希望自己的作品对读者能产生深远的影响。然而,并不能因为青少年文学不够艰深晦涩,就说它是肤浅而无意义的,正如深奥的作品并不见得就一定是有意义的。一位20出头的作者在会谈中哀怨地向麦高恩抱怨道:“人们读得开心不就够了吗?”确实如此,谁会在乎青少年文学到底该如何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