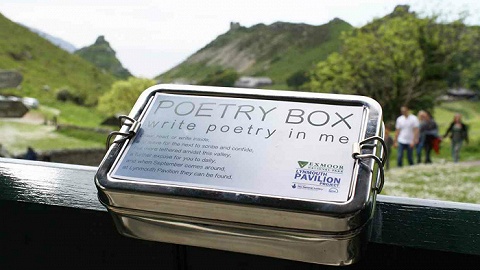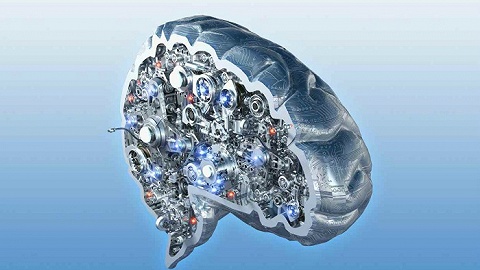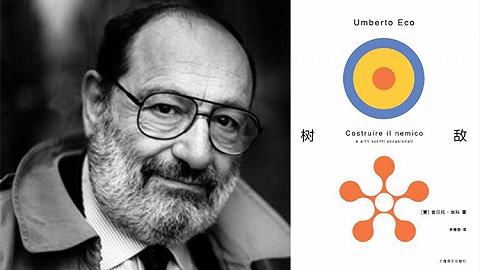数千年来,人类都坚信,他们的权利来自于神的赐予。随着人类步入现代社会的进程,人文主义取代了这种想法。卢梭在他1762年的作品《爱弥尔》中,总结了人文主义的特征,他这样写道“拷问我内心深处的,没有人能够影响,抹消的自我——我发现,我只需要按想法行事;我认为好的东西就是好的,我认为不好的东西就是坏的。”而此后的人文主义者们也秉承这一观点,像卢梭一样,他们相信人们的想法与欲望是存在的最高法则,而人类的自由意志也因此是人们最重要的权利之一。

但这一想法逐渐被新的学说所挑战。正如君权神授论为宗教介入世俗所提供了理论依据,人文主义者让天赋人权成为共识一样,硅谷以及高科技巨头开始为人们带来了一种新的世界观叙事,并试图为算法和大数据赋予更高的地位。这一全新的“教义”被命名为数据主义(dataism),原教旨的数据主义者(dataist)们坚信,我们所生活的宇宙是由数据流所构建的,有机生物不过是生物电反应的进一步呈现,而人类的使命则是创建一个数据处理系统,并最终融入其中。
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每个人都已经成为了一个(没有人能够理解的)巨大芯片组系统中的一枚芯片。每天我们要从电子邮件,电话以及网络文章中获取大量的数据,并将这些数据以更多的电子邮件,电话以及网络贴文的方式传递出去。我不知道人类是如何完美地适应这个数据系统的,更不知道我所创造的数据是如何与世界上数十亿人和电脑连接在一起的——我甚至没有探求这个问题的时间,因为我每天都有太多邮件要看。事物的生成与破坏都在数据的流动间完成,没有人能够计划或者掌控它们的运作方式,也没人能够理解。
不过事实上没有人需要理解这些东西,我们需要做的无非是更快地回复电子邮件或者信息。正如那些相信自由市场由“看不见的手”所调控的资本家们一样,数据主义者们相信有一只同样无影无踪的“手”在掌握着数据的流动。随着全球信息传递系统越来越庞大,越来越完善,与这一系统的连接就成为了第一要务。一则新的流行语这样说道:“如果你体验了什么东西,赶紧将它记录下来;如果你记录下了什么东西,赶紧把它上传到网络;如果你传的什么东西到网上,赶紧把它分享给你的朋友。”
数据主义者们同样相信,如果有足够大的存储空间以及足够强力的运算能力,这一系统最终能够理解人类——甚至比人类自身还了解人类。到那个时候,人类就将让出自己万物之灵的宝座,诸如民主选举一类的人文主义实践,将会像祈雨舞或是燧石刀那样退出历史舞台。
6月,英国退欧公投刚刚开始之时,迈克尔•高夫(Michael Gove)宣布自己将竞选保守党党魁一位,他在自己的竞选声明中这样说道:“在我的政治生涯中,每次我要做出重大决定之时,我总会问自己,此刻做什么事情才是对的,我的内心给我的是怎样的答案。”如果此话属实的话,他内心深处的自我让他为脱离欧盟大当旗鼓手,也促使他背叛此前的政治盟友波利斯•约翰逊,并希望借此上位。
高夫当然不是第一个号称“在关键时刻追随自己内心”的人。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人文主义者都认为,不仅仅是政治上,在各种领域内,凭人类的本心发誓都是表达立场的最高形式。从我们牙牙学语之时起,我们的生活就被人文主义标语所轰炸——“倾听自己的内心”,“对自己真实点儿,信任自己”,“追随你的内心”或是“做你想做的事情”。

在政治领域,我们相信政治家的权力来自于选民们的投票;在自由市场原则下,我们相信消费者总是对的。人文主义者同样相信,美是因为有发现美的眼睛;人文主义式的教育让我们认同应该为自己考虑;人文主义的观念则教导我们,只要某事能让自己开心,我们就尽管去做。
但人文主义观念的吊诡之处,就在于让某人开心的事情,很可能会让另外某人不开心。在这种情况下,人文主义价值观常常会碰壁。比如说,在过去的几年里,以色列的LGBT社群每年都会在耶路撒冷的大街上举行同性恋游行活动。而在这一天,存在于耶路撒冷的几个水火不容的宗教——基督教,犹太教以及伊斯兰教——总会一致地对同性恋游行表示愤怒,因为他们的教义不允许同性恋的存在。
有趣的是,近年来,宗教人士在表示他们对性少数群体的意见之时,不会直白地说“基佬们不应该在圣城街道上游行,因为神不喜欢同性恋”。他们会这样说:“看到同性恋同胞们在耶路撒冷神圣的街道上走过伤害了我们的感情。同性恋同胞们希望我们尊重他们的感受,但我也希望同性恋同胞们尊重我们的感受。”
关于这个问题,你的观点如何并不重要。但这个问题对于理解人文主义来说有着重要意义:在人文主义社会中,政治,道德,社会本身出现的争议,主要与人类的不同感受有关,而这一问题在宗教戒律上更为明显。
但人文主义目前正面临有史以来最大的威胁,“自由意志”也同样如此。最近,一些对人类大脑及身体的研究发现,人类的“感受”并非人类独有的精神属性。生物学研究则发现,哺乳动物和鸟类主要通过生物电反应机制来帮助他们做出决定:他们会在潜意识中计算不同行动的成功率,并以此做出影响自己生存繁衍的决定。
与大多数认为的那样不同,“感受”并不是“理性”的反义词,感受是人体经过理性分析之后所呈现的表征。假设一只狒狒,一只长颈鹿或是某个普通人看到一头狮子,身体就会计算出“死亡几率正在提高”的结果,而“因为害怕而颤抖”则是这种计算的体现。
同理,两性之间一见钟情,有很大可能是因为人体自身计算发现对方与自己合拍的可能性较大,进而表现出来的。在数百万年的进化之中,人类的生物电计算得到了加强与进化,若我们的祖先因某种感受犯错的话,这种感受将不会被基因所传承到下一代。
人文主义者将感受的出现错误地归功于“自由意志”,但这并不影响人文主义思想维系人类社会的运营。人类目前并没有比“自由意志”更好的做决定方式,也没有任何外物能够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自己。就算是克格勃全天候二十四小时地监视我,他们也不能通过我的某个动作来精准地定位我的欲望和选择——因为他们既没有生物学知识储备,也没有足够强大的计算能力。
因此,“跟随你的内心”这样的说法至今是没有问题的。刻薄点说,对于人生大事来说,“听从内心的声音”要比“听从《圣经》的教导”靠谱很多。原因很简单:人类的感受是千百万年来的进化所形成的,而《圣经》的观点主要是数千年前一些耶路撒冷神职者的感受与意见的集合。对于非教徒来说,两者之间谁更有信服力,并不需要解释更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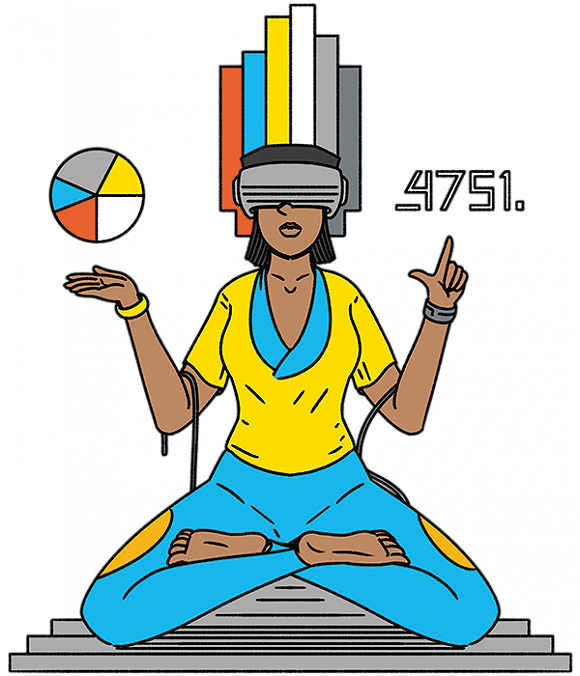
不过当教会或者克格勃式微,掌控人类命运的变成了谷歌和脸书之后,人文主义思想的实践优势即将荡然无存。当下,我们生活在两波科学浪潮之中:生物学家目前对于人类身体奥秘的破译,尤其是人类大脑与感知的研究进入了全新的阶段;与此同时,电脑科学家们为人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数据传输及保有的能力。两者结合之后,你就拥有了能够解读人类感受的利器,机器前所未有地比人类更加了解人类。而一旦大数据对人类的解读比人类对自己的解读更加真实可信的话,人类的自由意志就要向数据运算让位。某种程度上,大数据即将成为“老大哥”。
在医学领域这已经成为了既成事实。目前,决定医治某个病人的方法已经不再取决于病人自身对疾病的感受,甚至也不再取决于医生对于病情的预测和推断。由于更加精准也更加稳定,电脑的计算取代了人们对自己的判断。一个来自女星安吉丽娜·朱莉著名的例子可以对此进行佐证。2013年,安吉丽娜·朱莉在基因测试的过程中发现她携带有高危型的基因突变BRCA1 ,而根据医疗数据显示,大约有87%带有此基因突变的女性将会患有乳腺癌。当时,安吉丽娜·朱莉并没有患癌症,但为了避免这一风险,她仍然决定将她的双侧乳腺切割。安吉丽娜选择了相信电脑的运算:“虽然目前你并没有感受到自己得病,但你的DNA中埋藏着一枚定时炸弹,你现在就得快速作出选择。”
而在更多领域上,数据也开始发挥作用。比如挑书这一行为就是个例子,一个典型的人文主义者如何挑选他购买的书籍呢?他们会走进书店,漫步在书架之间,眼光快速掠过书脊,偶尔挑出一本书来翻看几页,这一行为会持续的时间不定,但总而言之,读者们会最终发现与自己灵魂相契的那一本书,结账走人。但亚马逊让更多人成为了某种数据主义者,当我打开亚马逊网站,网页自动会跳出一条消息告诉我“你之前看过了这些书。看过这些书的读者们会更喜欢下面的这些作品。”
而这仅仅是一个开始。除了网站之外,像是Kindle这样的电子阅读设备同样也会收集数据——甚至收集读者的阅读习惯相关数据。他们会发现读者在哪些部分耗时较长,哪些部分匆匆掠过;在读到哪些句子的时候停顿片刻,而读到哪一页的时候自此放弃书籍不再阅读。如果未来的Kindle设备加装脸部识别系统以及心率测试系统的话,这台装置甚至能收集读者在阅读作品时面部表情以及心跳快慢的变化,进而对阅读这本书某一部分的情绪基调作出总结。更关键的是,我们读过一本书往往过几天就忘了, 但电脑程序不会忘记数据。这些数据能帮助亚马逊公司更好地挑选适合某一个读者的具体书籍——甚至帮助亚马逊公司真正的意识到你是谁,如何调动你的情绪。
在这种逻辑之下,人们恐怕渐渐地会让数据和算法引领自己的生活,并利用这些东西来为自己做决定——比如说,寻找结婚对象。在中世纪的欧洲,牧师和家长往往拥有为一个人挑选结婚对象的权力。而在现代人文主义社会,我们对此问题的解决方案往往是“听从自己的内心”。而在一个数据为王的社会,人们或许会打开谷歌,并这样问道:“谷歌你好,现在约翰和保罗都想和我约会,而两个人我都不讨厌。我现在不知道该如何是好,请告诉我你所知道的关于这个问题的一切,并向我提出一些可行的建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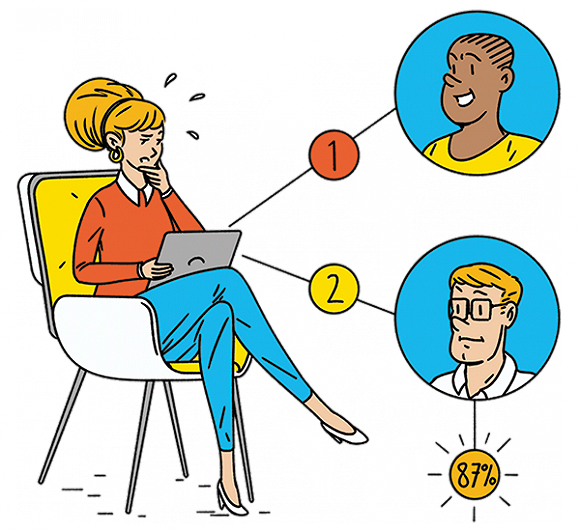
而谷歌的回答可能是这样的:“从你出生那天起我就认识你了,我阅读过你的所有电子邮件,录音过你的所有通话,我知道你喜欢的所有电影,你的DNA特点以及你从小到大每时每刻的身体状况。我了解你之前与两位男性每一次会面的情况,也能为你展现每次会面中你的心率,血糖以及身体其他指标的变化。当然,由于我强大无比的据库以及算法,我对约翰和保罗同样有着跟你程度一样的了解。根据我数十年来对各种婚姻关系的测算,我建议您选择约翰,因为你和他在一起占有87%的可能性成就一段爱情长跑。”
“当然,我非常了解你,我知道你不喜欢这个答案。保罗比约翰长得更帅,而你对于体重问题一直斤斤计较。你当然希望我给出的答案是“保罗”。不过外表问题跟你所想的并不一样,根据你自身对于自己的评价——从人类起源于萨瓦纳大草原之时即是如此,你认为人类美丑的判断中,体重因素占35%。但是根据我的计算,外表因素在维持一段长期恋爱关系中所占的比重仅为14%。因此,虽然我把保罗的外貌因素列入了计算,但我仍然认为约翰比保罗更好。”
谷歌不需要十全十美,甚至不需要每时每刻都是正确的。只要它做决定的成功率比人类自己做成决定的成功率高,它就能够成为大多数人的生活指导——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们不仅不了解自己,在人生遇到重大问题,需要做决定之时,他们往往也会把自己的生活搞得一团糟。

对于政客,商人以及普通民众来说,按照数据为王的观点看世界自然有其独特吸引力。这一技术实践极具创新性,而造成的结果也极为动人:人们往往害怕自己的隐私受到侵犯,也害怕自己的自由受到钳制,但对于大多数庸碌之人来说,如果让他们在健康和隐私之间作出选择,他们往往会选择健康。
而对于智库和学者来说,数据主义的出现似乎为人们揭示了科学桂冠的位置——用数据几乎可以解释各种学科的问题,从音乐学到经济学,从经济学到生物学,通通如此。按照数据主义的观点,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债券交易泡沫以及流感病毒只不过是三个数据流的呈现方式,人们甚至可以使用同样的工具分析模型对他们进行分析。数据主义为科学家们提供了真正的“通行语”,利用数据,他们可以轻易地将研究领域延展到其他学科,并更方便地跨越学科障碍,进行探索。
但正如之前所有的蛊惑人心的理论一样,数据主义或许建立在人们对于生命的误解之上。举例来说,数据主义无法对一个亘古的难题进行解答——意识。
目前,人类对于意识的解答仍然虚无缥缈,即使运用数据相关程序也同样如此。比方说,我们仍然不知道为何大脑中数十亿个神经元会因为我们的欢乐,悲伤或是愤怒而传递出特定的生物电信息。但即使数据主义最终被证明是错的,它仍然有可能征服世界。历史证明,宗教和意识形态政党经常犯错,但它们仍然有数以千万计的拥护者。而在更先进的科技的支持下,数据主义为什么不能达到这一目标呢?统一的科学范例当然有可能达成统一的“意识形态教团”。
如果你不喜欢这样的未来,并希望停留在数据算法的彼岸的话,那这里有个小小的建议给你——认识你自己。如果你对自己有着足够的了解,并具有比电脑运算还强的稳定性的话,为自己做决定当然是不坏的选择。要知道,数据称王的主要原因一定是下面这句话:
人类总是看不清自己。
本文作者简介:尤瓦尔·赫拉利,1976年生,牛津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历史系教授,全球瞩目的新锐历史学家。他的《人类简史》一书让他一举成名,成为以色列超级畅销书,目前这本书已授20多个国家版权,拥有大批青年粉丝。
(翻译:刘言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