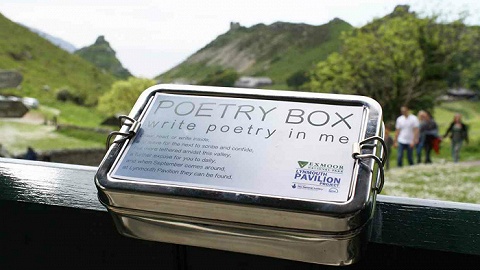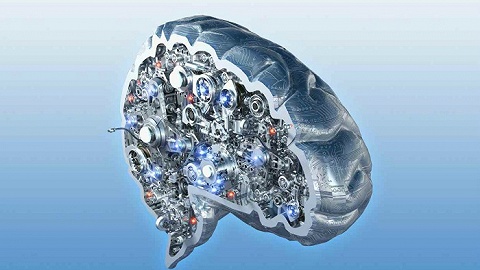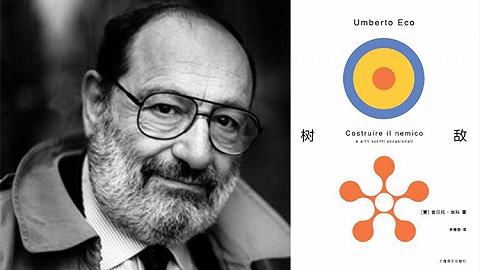近年来“国学”大热,这反映出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国人的财富的日渐增长,精神上流离失所已久的人们寻求本民族文化价值认同的迫切需求。
不过,那一个个闹哄哄粉墨登场的“国学院”、“儒学班”所夹带的扑面而来的权力欲和铜臭味往往令人觉得斯文扫地;而混迹这些名利场的又多是一些不学无术的江湖术士,更令真正的孔孟之徒悲哀。
因此,当我读到同济大学中文系张生教授9月13日发表在“冰川思想库”上的《儒学热:拜孔夫子,还是拜孔方兄?》,对其批评我的母校复旦大学作为一所全国一流的知名高校轻率地开设“上海儒学院”的基本观点十分赞同。
然而,我不同意张生在文章中表达的更为深层次的反对理由。在他看来,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含有太多“泥沙”与“沉渣”,过多地弘扬它们不利于培养现代社会所需要的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他甚至引用了胡适先生近百年前的评论,将政治儒学称为一种让人稳当地做“奴隶主”或“奴隶”之术。对此,我尤其深不以为然。

胡适
我认为,这种肇始于五四时期的激进反传统思想在过去百年中国艰难曲折的现代化进程中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而且贻害无穷。我既不同意将“传统”与“现代”对立起来的二分法,也不同意认为可以将传统文化的内容明确地区分为“精华”与“糟粕”的二分法。
在我看来,这都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被决定论谬误——不管是经济决定论还是文化决定论——所支配后产生的虚妄幻觉。事实上,传统与现代之间、传统文化各部分之间存在着远比这种削足适履的二分法更为复杂和有机的关系。传统文化在现代生活中的确需要经历一个重组和调适的过程,但这绝对不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那么简单的问题。
但本文的重点并不在此,我更多地想谈一谈我为什么反对高等院校设立专门的“国学院”或“儒学院”的理由。
目前中国的大学和科研院所都是按照现代西方的学术规范来设置学科分类的,用马克斯·韦伯的话来说,这是一种“理性化”的要求。它当然也存在许多问题,甚至是无法克服的根本性悖论,但迄今为止恐怕舍此别无其他更好的办法。

曲阜师范大学国学院
按照这个原则,大学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设置了哲学、政治学、伦理学、历史学、文学……等各种专业边界相对明晰的学科。
反观儒学,作为一种统摄中国精神世界(至少是上层)2000年的不断发展演化的传统文化,它是一种涵盖了信仰体系、政治治理、社会伦理和个人修养的包罗万象的文化存在,它既是一种宗教价值,也是一种政治哲学;既包含了学术成分,更是一个实践过程……历代大儒不厌其烦地强调的“知行合一”便揭示了这种文化存在的独特属性。
儒学的这种特性决定了它不可能作为一个专门的学科被吸纳进现代大学体制,因为说到底它不是一门学科。而现代大学是从事教学和科研的专业机构,它既不是寺庙和教堂,也不是古代的官办太学或民办书院;大学的使命是培养各学科的专门人才和进行各种科学研究,而不是通过耳濡目染、言传身教的熏习,为社会塑造出一代代为人师表、众人景从的“圣人”和“君子”。
正因为这个缘故,硬把儒学塞入当今的大学体制,一方面会割裂儒学作为一种信仰、知识与实践合一的文化传统的整体性和有机性,将它降低为一门苍白琐碎的专业学问;另一方面还会对大学现有学科设置的系统性和科学性造成损害。
更何况,如果这么做一开始就怀有鲜明的现实政治和商业动机,则必将对大学和儒学造成双重败坏,正如我们眼下已经看到的那样。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大学儒学院里的课程应当如何设置?学科标准应当如何设定?对毕业生应当授予何种学位?儒学院在讲学中可不可以对儒家经典发表质疑?儒学院的师生能不能信奉被正统儒家视为异端邪说的其他价值观念?逢年过节要不要拜祭天地并对圣人牌位三叩九跪?……这些问题都必将严重冲击理性化的大学体制。

2014年,都江堰国学院的拜师礼。
我与张生同样反对在大学里设立不伦不类的儒学院,但我与他的最大分歧在于,我不反对大力弘扬儒家传统。相反,我认为这是令人欣慰的好事,也是现代中国人寻求心灵家园的内在需求,一个民族不能长久地失落在信仰世界的荒原里。
只是,传统文化复兴注定要走过一段艰难而漫长的路途,不能以急功近利的心态去对待它。大学尤其要严肃地恪守自己的本分,而不是急不可耐地加入到将传统文化庸俗化的社会大潮中去,那是在进一步戕害本已支离破碎的传统文化。
我不想做国师和策士,对此也开不出什么药方。但在结束本文之前,我想用一句孔夫子的话与读者共勉:“礼失而求诸野”。我觉得,传统文化复兴的重大使命,未来恐怕要更多地由民间社会肩负起来。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公号“冰川思想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