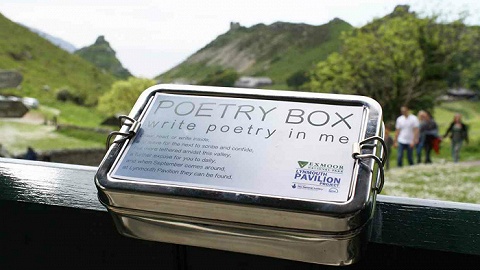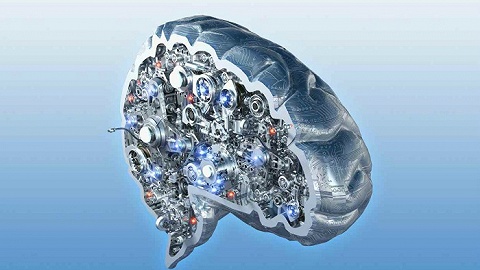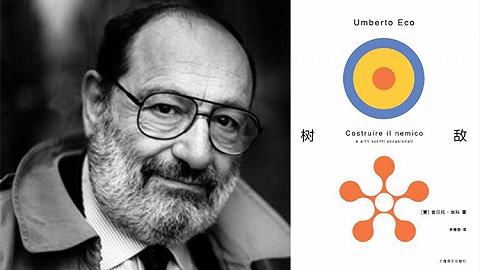编者按:在国内第一套“左翼前沿思想译丛”问世前夕,华东师范大学吴冠军教授、姜宇辉教授与南京大学蓝江教授进行了一场“当代左翼思想三人谈”,在对话之中,哲学、政治和艺术激进碰撞,随着三位对谈的不断深入,“左翼”复杂而迷离的前世今生在我们眼前逐渐展开。
蓝江教授梳理了左翼的思想谱系——从卢卡奇到早期的法兰克福学派,再到德里达和鲍德里亚,他尝试从中为我们解答这些问题:上世纪八十年代,面对新自由主义的话语体系和政治哲学,左翼为什么失去了抵抗力与话语权?左翼思源只有“人本主义”这一条路吗?新左翼的繁荣要依靠何种路径?
吴冠军教授指出了“左翼前沿思想译丛”的政治特征——对现实秩序的激进不满,这种态度令人们不断反思生活本身的政治性,“所谓的美景、美食背后真的就是中性的吗?是让我们享受生活这么简单吗?它们本身是不是也是一套控制机制,使得我们安足于当下我们的位置,不做任何他想。”那么,我们该如何避免成为共谋?又该期待怎样一种更好的制度呢?
姜宇辉教授从整个法国思想传统与艺术的关系发端,举例福柯、德勒兹、朗西埃等等,试图说明激进理论跟当代艺术之间水乳交融的关系。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如今思想界、尤其是中国哲学圈的保守,姜宇辉对于学术圈内、杂志纸上说来讲去的理论深感厌倦,于是把“噪音”艺术作为突破口,“在无处可逃的牢笼之中撕开一个裂口”,“为什么现在跟艺术家一起合作乃至创作,就是因为没有任何可能再激进下去了。”
以下内容为三辉图书和中央编译出版社对于此次对谈活动的发言整理,经授权发布。
蓝江:左翼的思想谱系
大家一谈西方的左翼,可能印象还停留在法兰克福学派那个阶段,包括萨特、梅洛-庞蒂这些人的阶段上,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或者左派就是指这帮人。但是我在想一个问题,实际上这些资源可能已经被西方超越了,他们的一些主要的话语是遭到了置疑的。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那个时代从卢卡奇开始,一直到法兰克福学派甚至到梅洛-庞蒂的早期,再到萨特,他们喜欢谈的“异化”、“拜物教”、“物化”这样一些概念。用我们这个社会是物化的社会,是异化的社会来批判,来批判意识形态,但是这样的问题展现出来,一定会遭遇到“究竟存不存在一个没有被异化的本真的我”的问题。我觉得今天我消费一个名牌包包,我住一个大房子开一个好车,就不是本真的我了吗?

在我们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经常有人跟我提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一定要认为,一个没有异化的我才是本真的我?他们不认同,尤其是那些“成功人士”说:我已经很成功了,我天天很享受,天天在我的阳台上喝着咖啡欣赏着夕阳,这是多么惬意的生活,而且不是在上海欣赏夕阳,我们在澳大利亚黄金海岸欣赏夕阳,这个就是本真的我,为什么这个东西你说我是物化的?
所以说在法兰克福那一代人,包括到鲍德里亚这一代人看来,他们这个批判遇到了一个瓶颈。其实他们的说法是对的,但是更多人不认可他们的批判路径。左派实际上最早开始是搞政治运动的,搞共产主义运动,搞社会主义运动,搞无政府主义运动,但是到了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左派变成了一个艺术、文学或者诗歌、电影的运动,这帮人全部蜷缩在艺术里,用审美来进行革命。
我们在哲学资源上面,可能会遇到这样的瓶颈,我们以“物化”、“异化”、“对象化”、“拜物教”这样的概念来重新审视,这一做法出现了问题,或者说这样的东西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变成了美国的文化研究,像伊格尔顿、詹姆逊这样一些人,他们在学院体制内把它变成另外一种很体制化的东西,把文化研究变成了一个非常学院化的东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意味着,在原有的理论架构的基础上,左翼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已经走不下去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左翼在面对当时已经慢慢升起的新自由主义的一种话语体系政治哲学的时候是没有抵抗力的,那个时候左翼当然只能求助于所谓的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来抵御这种政治哲学的吸引。
当时,以罗尔斯为代表的正义论,政治自由主义,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交往行为理论代表了西方政治哲学的主流,左翼在这个方面是没有份的,当然我们现在也可以说罗尔斯、哈贝马斯包括后来的理查德·罗蒂这样一些人都可以称为左翼,因为他们相对于另外一部分人是左的,比如说相对于查尔斯·泰勒。但是他们的左翼是在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上的一种左翼,是在现代的政治哲学框架下来解决问题的,所以后来,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左翼只能求助于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去摧毁一切。我们现在的力量就是摧毁,到德里达,到鲍德里亚不行了,敌人有城堡,我们现在没有武器了,我们弹药库空了,我们只有砸,砸碎敌人的堡垒。鲍德里亚他们干的都是这个,告诉你们看到的都是拟像,你现在只有把它当成拟像就行了,当它不存在。
所以我的判断是,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左翼经历了一个弹尽粮绝的阶段,异化的人本主义的或者是一种人道主义的理论路径走不下去了,怎么办?当然左翼不只这一条路径,我们称为“人本主义”或者“海德格尔存在主义”,对左翼思源进行影响的这条路径可能是油尽灯枯了,但是不等于左翼没有其他路径。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左翼新一代人的繁荣,实际上是在另一个资源上成长起来的,不是阿多诺的传统,不是海德格尔的传统,也不是鲍德里亚、德里达的传统,它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开荒重新起来的传统,这个传统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一种新的哲学的问题。
那么这个哲学是什么?当然,巴迪欧和他的学生梅亚苏已经给它一个很好的名称,叫做“思辩唯物主义”或者叫“思辩实在论”,也就是说他们现在开始走向了一个realism,用这个概念重新来架构左翼的资源。
反过来再去追溯齐泽克。齐泽克去年的两本书,包括更早出来的书都会谈到一个话题叫“辩证唯物主义”,不是“历史唯物主义”,他的几本书全部把辩证唯物主义加进来,这本书的副标题就是“黑格尔与辩证唯物主义”,还有去年大概这个时候,叫“absolute recoil”绝对反动,它的副标题也是“一种新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奠基”,就是说,齐泽克也在谈这个问题,实际上他在这里谈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巴迪欧谈的思辩唯物主义是可以等同的,这个等同我现在在这里不能跟大家做详细展开。
我只能说这是一个当代左翼利用的全新资源,这种资源不同于我们之前讲的人道主义传统或者后结构主义传统的资源,当然这个资源的源头毫无疑问是拉康,当然像齐泽克会追溯到黑格尔,说黑格尔是一个很重要的唯物主义者而不是唯心主义者,这是齐泽克反复谈论的。
吴冠军:左翼的政治指向
今天我们这套译丛介绍的思想家,他们共享这样一个特征,对现实秩序的激进不满,这是一个政治的特征。
我们可能都觉得,在历史上来看,我们跟古代去比、跟中世纪去比,我们的日子过得真的很不错了,在座的每个人可能都觉得生活得还可以。但对这些思想家来说,这种理解太短视了。
他们通过许多精彩的分析告诉你,这套系统怎么让你满足,怎么让你觉得自己生活得还不错……让我们觉得很舒服的东西,其实是成问题的,为什么我们看到德波的电影说这就不是电影,听到噪音说这就不是音乐等等。而另外一些东西,则带给我们美感、快感……

这些所谓的美景、美食背后真的就是中性的吗?是政治上中性的吗?是让我们享受生活这么简单吗?它们本身是不是也是一套控制机制,使得我们安足于当下我们的位置,不做任何他想。那么这些思想家认为,我们需要做更多的工作。他们不是说这个世界是最糟的,比它更糟的还有——但这个世界还绝对不够好。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一个政治的态度,他们是对现状持批判态度的思想家,这是一个很清晰的界限。
所以开始蓝江老师说,我们今天中国讲左翼跟西方讲左翼,用的词叫“leftist”,我们觉得是一个词,但是这个对接,怎么对接怎么别扭。因为很多这边以左翼自居的思想家,他们不提批评,他们不提怎么使这个社会变得更好,在他们看来已经最好了——中国模式,没有比它更好的东西了,这样一个思想绝对不是一个leftist所拥有的思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区别。所以说作为这些激进思想家,他们所拥有的态度是很鲜明的。那么在具体的层面上,在论证的层面上,他们当然是有一个很系统的、哲学性的论述,比方说,这样一个世界为什么就不是一个终结性的秩序呢?
在他们看来,没有一个可能性使得任何的秩序可以自我宣称:“我已经到了一个历史的终结”。他们用各式各样的方式论证,比如巴迪欧用“event”这样一个概念,任何的情况下我们如果觉得这个世界好像从此太平盛世,从此太阳底下不会有新东西,马上一个巴掌打脸,肯定会有全新事件发生,事件的这种发生是任何的大国政客都没法控制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这个世界永远会带来惊讶,让我们目瞪口呆、让我们措手不及,这个世界不会终结。再如齐泽克用辩证法的方式论证,辩证法意思就是不管你说什么,说得再好听,总会被打脸,因为辩证法最关键的一点就是马上会有一个否定面出现,一个事物宣称自己好到极点的时候,你就等着看它怎么倒下去,这是辩证法的智慧。
所以,这些思想家们的哲学就是政治的,他们告诉我们说,今天所处的秩序不可能是最好的,不可能就到此为止,不再有更好的秩序出现。如果我们放弃了,我们在思想上认为这个已经好得不行了,其实我们就扮演了一个共谋的角色。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在理念上、在思想上永远是要告诉人们,有更多的工作等待我们去做,而且我们做的不是小修小补的工作。
这个秩序你们真的觉得很好吗?
所谓的今天的“全球资本主义”这个秩序,当然它带来很大的生产力,但是你们都没有看到整个世界分化得怎么样了。精英阶层越来越“精英化”,而且是一种变态的“精英化”——因为今天“精英”二字,只和财富有关,和道德、学问统统无关。中国也一样,这个“精英”变成越来越少数的一小撮。中产阶级?在来的路上我和蓝江还在比工资,我们经常比工资,越比越觉得:我们还是中产阶级吗?社会的差距越来越大,资本的掠夺方式越来越新颖,你去看看以前那些资本家、那些大家族,几代人拼命一代接着一代地积累。
今天看看,马云那么快的就变成巨富,通过什么方式,他们对社会财富掠夺的速度要比前几代人快得多得多,这把刀快得不得了,我们完全没有感觉。我们认为他们就是做了我们没有做的事情,认为他们比我们创新了更多,但事实真的如此吗?那些媒体光鲜故事背后的暗黑“博弈”翻开来,你真的能细看得下去?在美国一样,我们认为他们市场很公平,你仔细到背后看一看,一点都不公平。今天滴滴跟优步又合并了,不断的合并是为什么呢?就使得这个市场越来越趋向少数精英,“干不掉对方就加入对方”,不断“合体”,合体完以后我们永远是最痛苦的承受者。这个社会已经形成了一个我们没有注意、但却悄悄发生的一个大变化,就是他们掠夺的方式越来越变得跟以前不一样。
以前,至少我们还能看到他们对工人赤裸裸的剥削之类的,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所提出的,那时候的工人常年在工厂里面,跑出来这张脸都很吓人,充满皱纹、呼吸粉尘。今天,自动化越来越多,感觉这种最痛苦的人越来越少,除了还能在建筑工地上看到。在一般意义上,大部分人都已经到办公室上班了,那种完完全全穿得很破破烂烂的下车间钻厂房的工人越来越少了,但这不代表这个世界走向越来越文明,这只能说明它掠夺的方式越来越精密化了,或者说它越来越少地需要你们这些人一个个去工作了。但是资本主义还是需要你们作为什么呢?不是作为生产者,而是要你们作为消费者,否则它生产出来的东西谁去买呢?
所以说它以另外一个方式不断地要你参与进来,用各式各样购物的方式把你卷进来。通过这个方式其实我们更加的痛苦,因为它对生产劳力需求的降低,我们今天发现越来越多的人找不到工作,不是他/她自己要去创业,是被迫去创业,因为求职越来越难,不需要那么多人。
姜宇辉:左翼与当代艺术
刚才蓝江和冠军其实已经给了我们一个图景,但是我觉得说得还不够。因为像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的最后说,“我们已经无路可逃了,所有一切都可以成为商品,都可以成为消费市场里面的一部分”。包括我上次跟三辉做的活动,讲克拉里《24/7:晚期资本主义与睡眠的终结》这本书,他也给我们描绘了一个前景:马克思说在生产劳动领域里面有异化,后来到法兰克福学派,则是进一步说在日常生活里面也会有异化,比如阿多诺、霍克海默对文化工业的批判就是明证。但是克拉里他说即使我们在睡觉的时候,资本主义的魔爪也是无孔不入的。
所以,为什么要搞噪音?就是要给自己提供这样一个极端的突破口,在无处可逃的牢笼之中撕开一个裂口。
我搞噪音就是觉得作为一个学术壁垒之内的大学老师,在杂志上去说去讲去写这些激进“理论”,多少已经觉得非常厌倦。为什么现在跟艺术家一起合作乃至创作,就是因为没有任何可能再激进下去了。但其实我们整个都是在机器里面运转的一个部分,那么又在什么意义上能够摆脱出来,有资格、有理由说自己是很激进?包括我们脑子里面是不是天天也想着工资、孩子、待遇这些东西?…… 其实我是觉得很厌倦,所以我自己很迫切地需要这样一个出口。

刚才提到了艺术或者美学。其实即使不局限于激进理论的范域,就整个法国思想传统而言,从启蒙运动或者从更早的时候开始,哲学和艺术在法国思想里面一直都是相通的。与其问法国思想家里面哪个不懂艺术,还不如去问哪个对艺术有一些更深的理解,哪一个更精通艺术更好一些。我读到六七十年代或者更晚近的思想家的作品的时候,发现这一点其实是非常明显的,比如说在福柯那里,他研究过很多的画家;德勒兹就更多了,甚至还专门写过电影、绘画方面的专著;甚至像后来的你们激进阵营里面也有很多思想家对艺术很感兴趣,比如朗西埃他以前就是在意大利学电影的。所以激进理论其实跟艺术之间,尤其是跟当代艺术之间有着水乳交融的关系。从根本上来说,这突出一个现象,即不论在国内还是国外的艺术界,它从精神上总是更为倾向于激进思想,更需要批判的锋芒来推进他们的创作。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今天的学术圈,尤其是中国的哲学“圈”反而显得愈发保守。因而,无论是生活还是艺术,我们都需要有一个推动的力量,能够进行转化的力量。当然艺术圈其实也很腐朽,尤其是当代艺术,简直就跟资本市场完全是一体的。像刚才冠军、蓝江批判的一些异化的现象,在艺术圈简直就是常态。不过即便如此,我们仍然还是能在当代艺术里面发现更为激进的思想萌芽。即便不说苟延残喘,至少在其中还能够呼吸一点新鲜的空气。所以我也衷心希望二位今后能够更积极地介入到当代艺术或者艺术圈的对话或者实践里面。
最后,我觉得如果按激进这个标准来说,我心目中最激进的思想家就是福柯了,因为福柯有一句话,他说我像狗一样的生活,像狗一样的工作,但是我只想实现一个目的,就是转化我自己(transformation of self),让我自己去摆脱这种陈旧的学术体制,摆脱异化的生活方式,通过学术、通过思想,通过生活方式的变革来推进自我的一种转化。包括他晚期讲的一些东西,其实都是他一以贯之的激进姿态的一个体现。所以我之前虽然批了一点福柯,但是在我心目中,我觉得他比齐泽克、巴迪欧、阿甘本都要激进的更多。在我心目中,我是非常希望能够成为福柯这样的激进的思想家,能够言行一致而且能够纯粹真实地追寻自己。最近出了一本福柯的书,叫做《说真话的勇气》,我觉得这个也恰恰可以作为激进思想的一个核心口号。
什么叫激进,我觉得就是有勇气,能够站出来说真话,能够面对世界的真实,面对自我的真实。当然我选择的是噪音,你们二位选择的另外一种激进的生活方式,都是殊途同归。

“左翼前沿思想译丛”将陆续与读者见面,由吴冠军、蓝江主编,三辉图书与中央编译出版社合作出版。这套译丛收录了阿甘本、齐泽克、巴迪欧、加塔利等一批欧陆左翼思想领军人物在过去二十年间的经典著作,系统性地向汉语学界引入关于当代左翼思想的最前沿成果,探讨“左翼的思想谱系”、“左翼的政治指向”,以及“左翼与当代艺术”。
“左翼前沿思想译丛”已出版三本,分别为《神圣人: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意]吉奥乔·阿甘本 著,吴冠军 译)、《对民主之恨》([法]雅克·朗西埃 著,李磊 译)、《剩余的时间:解读<罗马书>》([意]吉奥乔·阿甘本 著、钱立卿 译),其余9本将于今年陆续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