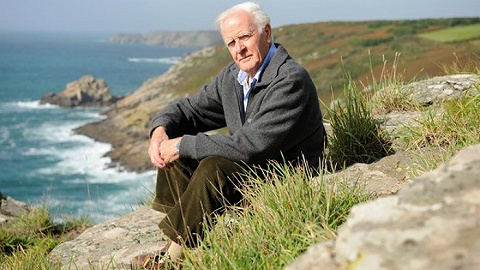来听林西莉讲座的大多数是带孩子前来的家长,她这次是为宣传新书《给孩子的汉字王国》而来。她开口说的是英语,简单问候过后便为自己不说中文而道歉,因为她有一段时间没来中国了。
林西莉说话急促,不时地微笑,笑的时候眼里洋溢着友善和热情,让人很难想到她已经84岁了。待她起身,才会注意她行动艰难,需要拐杖的支撑,半年前她做了第二次膝关节手术。后来坐在她对面采访时,她伸出手来——弹了几十年古琴的手,如今肿大僵硬,有些指头弯曲着,无法抻直,它们变形厉害,看起来怪异而缺乏生气,简直不太像一双手了。
自她初次来到中国,已有五十多年过去了。她写道,作为一个局外人,“我怎么样从把中国视为洪水猛兽、在很多方面都厌恶她,到比较好地理解她——最后不顾一切地爱上她”。
林西莉生于瑞典隆德,年轻时就学习了多年汉语言学及中国艺术,老师是著名汉学家高本汉。1961年,当她的第一任丈夫要来瑞典驻华大使馆工作时,她决定同往,到北京大学学习汉语。
那个时候要获得中国的留学签证非常难,她得到了很多人的推荐信,其中包括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六世。1961年1月2日,他们终于成行。路经莫斯科时,她去见了当地的一位音乐教授,说自己想在中国学一门乐器,教授建议说,应该学古琴,古琴是最能体现中国古代文人风骨的乐器,并向她推荐了古琴研究会。
1961年的中国对她来说完全是另一个世界,在瑞典时她读了不少关于1949年的中国的书,但1949年后的中国是什么情况,瑞典人都几乎一无所知。
她住进了北大的宿舍,教室和宿舍都很冷,学生们都穿得鼓鼓囊囊的。春天到来时,学生们爬到榆树上摘树叶吃,为了抓到树叶,很多枝杈被折断。林西莉跑去跟老师说有人毁坏树木,老师告诉她全国都在闹饥荒。然后她注意到她的同学们浮肿的面容和肢体,直到自己也开始一绺一绺地脱发时她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医生诊断为蛋白质严重缺乏,让她每周两次到协和医院注射维他命B。
在北大的经历很不愉快。课文中很少有日常用语,绝大部分课文都富于政治色彩。老师只是机械教学,一味让死记,没有过多的解释,提问被视为打扰课堂纪律。她在日记中写道:“我感到我与这个国家的距离在令人不安地增加。生活过得如此沉重,就像穿着胶鞋跋涉在泥泞的田地里…授课不是要造就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而是要使人无条件地服从新的社会制度…我感到我在变小、皱缩和正在不可救药地变成一个四岁的孩子。”

当林西莉进入北京护国寺附近的古琴研究会学习古琴后,她对中国的态度完全改变了。古琴研究会(成立于1952年,文革期间被关闭)在一栋老四合院里,一共有11位音乐家、学者,他们博学、友善、敬业,从不讲空话和口号。而她是古琴研究会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学生,他们恨不得把所知道的都教给她,毫无保留。
对她来说,这儿是与严酷的政治大环境隔绝的一方清净之地,中国最精英的传统文化尽管遭到怀疑,但仍然在此保存完好。
她的老师是王迪,王迪弹的是一张唐代的琴,林西莉弹的是一张宋代的琴。在隔壁工作的古琴演奏家、画家溥雪斋有时会轻手轻脚走过来评点一下,他是末代皇帝溥仪的堂兄。王迪的老师、杰出的古琴演奏家管平湖自然也很关注,时不时过来看看。她印象中的管平湖“不过一米五的样子,瘦弱矮小,满头灰白的头发。他把那双又大又黑像树根一样凸凹不平的巨手在琴弦上摊开时,反差极大。他的弹奏如此有力,仿佛整幢楼都要倒塌一般”。当时查阜西、吴景略是音乐学院教授,研究会里还有汪孟舒、杨葆元等人。这些人都温文尔雅,安安静静。她花了好长时间才明白这些老先生是何许人。
每天她抱着那张借来的上千年的宋代古琴穿行于人流中,费很大劲挤上公交。她沉迷于古琴的美妙声音和琴曲的意境与故事里,《平沙落雁》是关于大雁飞来,徘徊落下,又飞远消失,曲调伤感,《胡笳十八拍》讲的是被匈奴掳走的蔡文姬的真实故事,更为传奇的《广陵散》描述了战国时聂政刺杀韩王的故事,魏晋时嵇康临刑前曾索琴弹奏此曲。
在古琴研究会的那两年里,“我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深的崇尚之情,尽管当时我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五十多年后,一说到古琴研究会,她就会激动起来,语速也更快了。

1961年古琴研究会里星期天的音乐会,左二为管平湖,左三为王迪,右中为溥雪斋,右一吹箫的是查阜西。
两年后林西莉因家庭原因恋恋不舍地离开中国。古琴研究会不仅送了她一张明代的琴“鹤鸣秋月”,还为她灌制了一盘如今已成为绝唱的磁带。
1973年她第一次重返中国,她找不到王迪,古琴研究会已不在旧址,没人知道那些古琴家和他们搜集的文献去了何处。(溥雪斋和管平湖分别于1966年和1967年过世。)她年复一年地打听他们的下落,但一无所获。1978年她终于与下放农村归来的王迪取得了联系,得以重逢。
1970年代林西莉开始在瑞典教授汉语,汉字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她讲解汉字的结构和来龙去脉,从甲骨文、金文、小篆到今天的汉字,她还尽量利用中国新的考古发现,一些文物图片,使学生对汉字的形状来历有迹可循。“我发现我的学生的反应和我过去完全一样——我对汉字的结构和早期形式讲授得越多,他们越容易理解和记住这些汉字。当我同时也讲解这些文字所来自的那个世界,讲述古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他们的房子、车辆、衣服以及他们使用的工具,讲述产生这些文字的自然场景——乡野、山河、动物与植物时,效果就特别好。”

1973年她再次获得到中国签证,此后每年都会来一两次,到图书馆查资料,拜访专家学者,前往考古发掘地观察实物,在山东、陕西、河南等地设立考察点。如果发现一种工具或文物器具与某个字字形有关,她便会兴奋不已。十五年后的1989年,她完成了《汉字王国》,该书获瑞典文学图书最高奖——奥古斯特奖,并被翻译成十几种文字。
《汉字王国》完成后,林西莉开始写作《古琴》,讲述自己在北京古琴研究会学琴的经历。“‘鹤鸣秋月’这张琴,和那些我在北京古琴研究会有幸遇见的人,便是促成我写这本书的重要原因。”《古琴》的写作又用了十五年,并再次获得奥古斯特奖。她还请王迪的女儿、中央民族乐团的古琴师邓红到瑞典做了四十多场演奏,演出大受欢迎。下周邓红将又将前往瑞典演出,林西莉非常期待。
林西莉访谈
界面:你日常生活中还经常弹古琴吗?
林西莉:是的。但我的手肿了,不能张开,动起来也很困难。所以我只弹给自己听,不再为他人弹了。我喜欢为自己弹琴,这会使我平静快乐,并想起中国的文化和中国的朋友来,弹琴有点像是冥想(meditation)。
我在中国学习那两年,我的老师说,我们知道你想买一张琴,但基本上不可能买到,因为不会有家庭出售古琴,也没有人弹琴,下一代没准有可能;所以我们给你提供一张宋代的琴。我那时就带着琴上公交车,周围人们挤来挤去,很危险,我非常担心会碰坏我的琴,但什么也没发生。
后来他们送了一张明代的琴“鹤鸣秋月”给我,现在就在我家里。
界面:学琴的那段经历对你有多重要?
林西莉:我对这段经历记忆犹新,我当时发现这群教古琴的人是非常有教养,非常真诚,对古琴非常专注的文化人。他们也非常专注于把古琴作为一种文化,传递给给像我这样的外国学生。当时在中国很少有人对古老的乐器这么感兴趣。古琴教授不仅仅教我弹琴的技艺,也教许多琴背后的文化和知识,所以通过教授的讲解知道有着千年历史的乐器,到底是怎样发声、怎样讲述古琴背后的故事。
不夸张地说,在中国学琴这两年的经历,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经历之一。这两年改变了我的人生,我原来学习的时候并不是非常理解古琴这门乐器,后来我把古琴看作人生中的一部分,生活意义的一部分,跟以前的古琴教授一同去挽救这门即将要消失的中国古琴艺术。

林西莉在古琴研究会学习时。”后来我把古琴看作人生中的一部分,生活意义的一部分。”
界面:到古琴研究所之前,你在北大过得不大愉快,那段时间最糟糕的是什么?
林西莉:可以说,很不愉快。学生们都很胆小害怕,要是做错了什么,就会受到惩罚,或是被送到农村去。每个人都很害怕。我发觉有人动过我的箱子,衣服,平时吃的药,所有东西。因此我将一根线粘在我的箱子上,这样可以知道他们是否打开过它。当我回到宿舍,线不见了,箱子里被翻动过。我又把一个很小很小的纸片,那种卷烟用的纸,粘在门下面。我回来后发现,那片纸破碎了。最后我觉得我快要疯了。
我向留学生办公室抱怨这事,问为什么对我这么做。但他们说,我们从未对亲爱的学生做过这种事。但他们做了。他们想知道我的一切事情,有个女孩是安排来帮助我学习的辅导员,每周来三次,每次两小时。她人很好,但她每次问上百个问题,你到北京后都见过什么人,看过什么书等等。一个波兰学生在宿舍发现了他的“辅导员”落在那儿的一个本子,里头写了所有的细节,他见过什么人,对政治的观点等。
当时有三个瑞典人在翻译毛泽东的著作,我说,你们为什么要听当局的。有个人就说,这儿到处都有人,你说什么都有可能被他们听到。他很清楚当时的处境,我们都处于监视之下,很糟糕。
界面:要是没有学古琴的话,你还会在中国待这么久吗?
林西莉:古琴是我留在中国很重要的原因。如果没有参加古琴研究会,当时很可能就离开中国了。作为外国学生,人身自由很受限制,让我觉得非常不适应。
当时许多人饿死,商店里面没有东西卖,路上也没有公交车,也没有出租车,只有一些骑车的人。我是在春天来到北大学习的,我发现有些人趴在树上不知道在干嘛,那些人竟然在吃叶子,所以我要求老师阻止他们不要吃叶子。老师说他们从去年9月到现在一直没有东西吃,我觉得非常难过,完全不知道中国的状况是这样的。外国学生和中国学生住在不同的地方,互相之间的交流受到限制,我当时并没有完全了解中国当时的状况。

王迪指导林西莉弹琴
界面:你的老师王迪后来怎么样了?
林西莉:1978年教授从天津郊外一个农场劳改结束回来之后,我们重新取得联系。《古琴》这本书离不开她的帮助,她帮我准备了很多材料。2005年,出版《古琴》这本书的前一年,教授去世了。
我得知教授的女儿邓红也是古琴演奏师,所以就邀请她女儿来瑞典进行演奏,举办了非常多的音乐会,场场爆满。当时琴箫合奏在瑞典是史无前例的,许多大学还有组织都会来聆听来自中国的乐器。他们在瑞典全国连续举办了差不多三个月,从一个城市跑到另一个城市,一场接一场马不停蹄地演。去年他们去冰岛演出,下周还要继续回瑞典进行同样的演出,非常开心能重新见到这些非常有名的古琴艺术家。